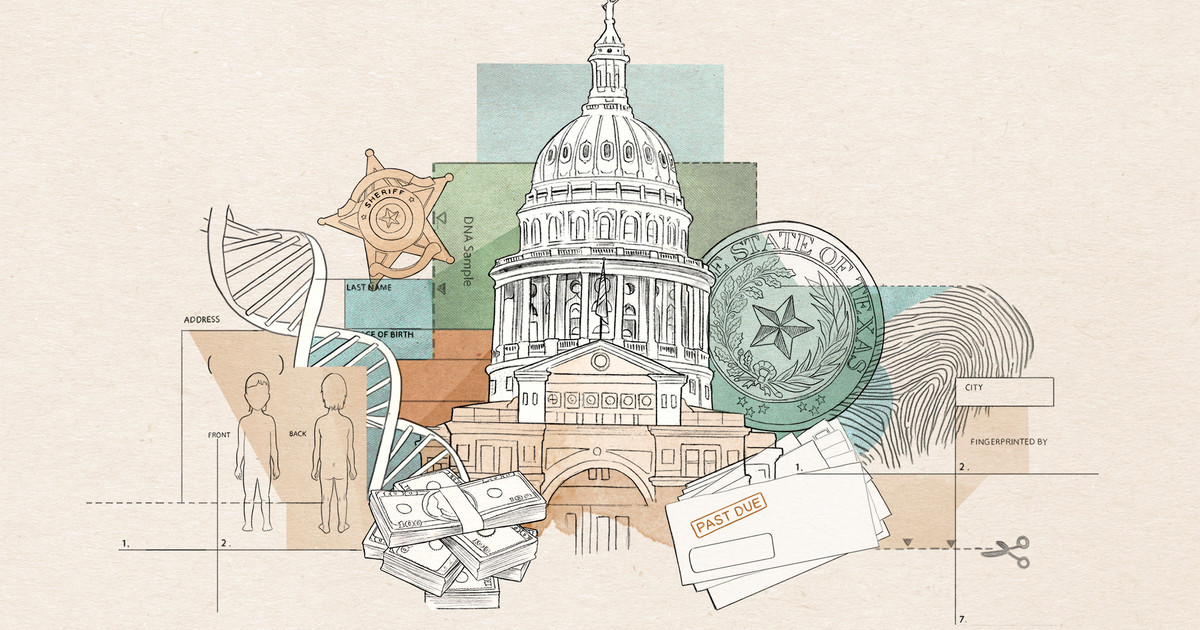不到一年前,雖然感覺像是十年前,美國最高法院允許總統在執行官方職務時免於受到刑法的約束。換句話說,總統不必擔心違法,因為他們永遠不會被追究責任。週四,川普政府再次向法院提出相關請求:法官們能否讓我們對未能提起訴訟阻止我們的任何人執行非法命令?
這一請求源於針對川普非法行政命令的訴訟,該命令拒絕未經授權的移民及簽證持有者子女的出生公民權。這顯然違反了憲法的公民權條款,該條款保障幾乎所有在美國出生的人的出生公民權,因此川普政府不希望法院處理這一問題。相反,他們要求法院剝奪司法機構頒發全國性或普遍禁令的權力——這些禁令能夠在法院考慮最終裁決的過程中中止規則、法律或政策的實施。
如果法院在最高法院決定某項命令違法之前無法中止政府的非法行為——這個過程可能需要數年時間,若案件能夠到達九位大法官那裡,那麼政府將可以自由地對任何無法訴訟或可能加入集體訴訟的人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情。這使司法系統從一個可以阻止非法政府行為的系統,變成一個只能為那些能夠挺身而出並要求救濟的人提供莫名其妙的補救措施的系統。
這是一個可怕的司法系統的願景。想像一下,警方識別出一名連環小偷。他在全國各地的社區夜間作案。警方並沒有將他逮捕,而是小偷僅僅承諾不進入那些打電話給警方投訴並獲得禁令的房屋。在陪審團定罪之前,其他地方的人都將繼續受到搶劫。這就是川普所要求的:在案件以某種方式到達最高法院之前,能夠不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行事,並不僅限於這一公民權問題,而是他能想到的任何非法或剝奪權利的計劃。
“你的論點似乎將我們的司法系統,從執行者的角度來看,變成了一種‘抓我就行’的制度,所有人都必須有律師並提起訴訟,才能讓政府停止侵犯人權。”大法官凱坦吉·布朗·傑克遜告訴檢察總長約翰·索耶。“我不明白這怎麼會與法治相一致。”
“你回到英國普通法和衡平法院,但他們有不同的制度。事實上,英國衡平法院無法對國王頒發禁令,我認為這與我們系統中的法院所能做的並不類似,國王,所謂的,執行者應該受到法律的約束,而法院有權說明法律是什麼。”
這是問題的關鍵。最高法院的共和黨任命的多數派不斷調整目標,使總統越來越像殖民地宣告獨立的君主。當川普在社交媒體上把自己描繪成國王時,他的政府卻在為他擁有國王的權力而不斷施壓。
在對抗普遍禁令的斗爭中,川普政府主張,對於非法命令的最終全國性救濟只有在最高法院判定其違法時才會到來。索耶確實承諾政府將遵循任何此類命令。但正如大法官埃琳娜·凱根在質問中所指出的,沒有任何保證最高法院會迅速審理對非法行政命令的挑戰,或者根本不會。
索耶和一些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似乎對這樣的想法感到滿意:通過某種途徑——個別原告或集體訴訟——對行政命令的挑戰可以迅速抵達最高法院,並在那裡得到迅速解決。但凱根迅速指出,政府實際上是在爭辯一個非凡的漏洞:違規行為越嚴重,問題就越難以進入最高法院。
出生公民權問題就是一個完美的例子,因為大多數律師認為這是無理且毫無根據的。“假設你在下級法院普遍失敗,就像你在這個問題上一直失敗。”凱根施壓道。“我注意到你沒有將實質性問題提起給我們。你僅將全國禁令問題提請給我們。我是說,為什麼你要將實質性問題提起給我們?你在很多案件中都在失敗。這位男士這位女士,他們將被視為公民,但其他人則不會。你為什麼要把這個案件提起給我們?”
換句話說,川普政府可以通過失敗來獲勝。如果失敗的一方,即政府,接受個別損失而從不上訴,那麼它將通過對沒有律師的所有人應用該命令而獲勝——尤其是在害怕被驅逐的移民群體中,大多數人都是沒有律師的。
在兩個半小時的辯論後,目前尚不清楚五位大法官是否會一致結束普遍禁令。這將是一次激進的法律改變,將使國家遭受川普及其智囊團可以想到的所有非法幻想的影響,持續一段不確定的時間。這一案件清楚地顯示了選擇的輪廓:大法官顯然不喜歡普遍禁令的廣泛使用,而共和黨任命的法官更是討厭對川普的連續禁令。但同時,出生公民權命令顯然是無理的。
或許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的問題最能體現這一僵局。作為一名原則主義者,托馬斯的問題集中在普遍禁令的歷史及其普通法的祖先上,似乎是為了反駁這一存在的合理性。
但托馬斯是否相信,正如索耶週四所述,公民權條款僅僅意在涵蓋曾經被奴役的人民的後代?兩年前,托馬斯寫道,包含公民權條款和平等保護條款的第14修正案彼此緊密相連,並且為所有人類提供了普遍的平等規則。“公民權的保證的增加因此表明了擴大的意圖,超越了剛剛獲得解放的黑人,並納入了對所有美國人的更一般的平等觀。”托馬斯在《哈佛學生平權訴訟案》中寫道,利用該修正案為結束平權行動辯護,強調其對白人的適用性。至於該修正案對於出生公民權的保證,托馬斯稱之為“新自由的誕生”。
但如果法院無法保護它,那就不值一提。
(内文照片来自GOO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