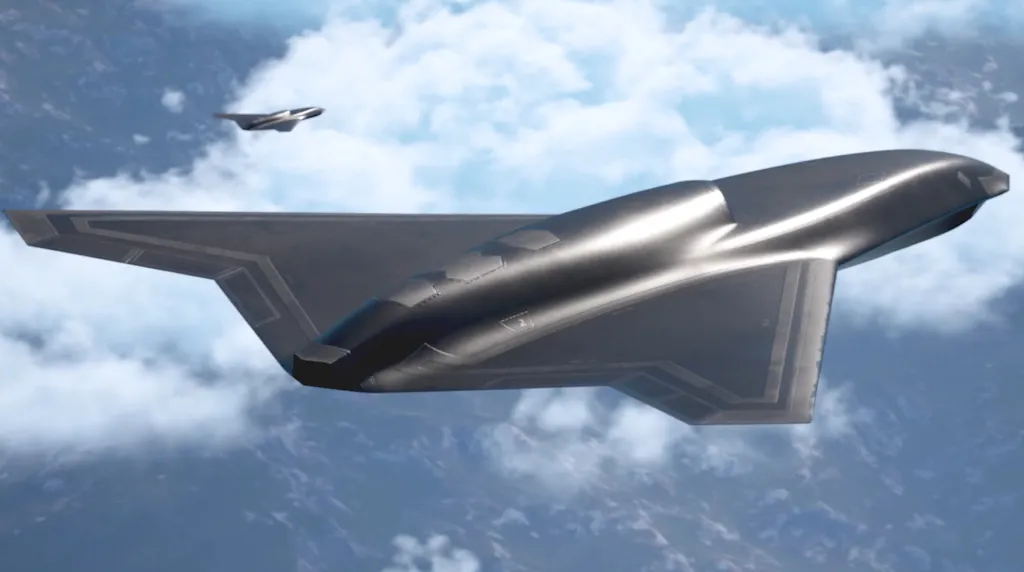從《魔鬼城堡:納粹優生學、安樂死及精神病學的動盪歷史如何在今天產生回響》一書中獲得的內容,出自Counterpoint Press。
特倫布林卡審判的檢察官阿爾弗雷德·斯皮斯(Alfred Spiess)向電影製作人克勞德·蘭茲曼(Claude Lanzmann)描述他的被告時說:「他們不是SS成員;他們來自安樂死計畫,習慣了殺戮,在1941/42年冬季被集中在一起,以便被送入滅絕營。這是納粹政權的長期計畫……而這群人習慣於在安樂死計畫的範疇內進行殺戮。」
特倫布林卡的死亡人數在納粹營裡排名第二,至少有八十萬人,最多可能達到九十五萬人,僅次於奧斯維辛的約一百一十萬人。
我們應該集體想要理解這個安樂死計畫,讓許多普通的德國工人和醫生能夠進行如此多的殺戮。太長時間以來,我們幾乎沒有好好檢視這個問題,尤其是在歷史反猶太主義的背景下。
正式的安樂死計畫始於阿道夫·希特勒的一個命令,這是希特勒親自簽署的第一個大規模謀殺命令。這份簡短的備忘錄於1939年10月發出,被追溯至9月,以便與戰爭的開始相鏈接。許多機構早已實施了臨時的安樂死。希特勒的用詞暗示了他們即將要做的事情,暗示了他們早已在進行的事情。這份安樂死的命令發送給了希特勒的隨行醫生卡爾·布蘭特(Karl Brandt)和希特勒私人總理府的首腦菲利普·鮑勒(Philipp Bouhler)。希特勒指示布蘭特和鮑勒「擴大某些醫生的權限,以至於經過人道的、最謹慎的評估後,可能讓被判定為無法治癒的病人獲得安樂死。」
這裡重要的字眼是「醫生」和「死亡」:『人道』、『謹慎評估』和『仁慈』只是無意義的修飾,就如同死亡證書上的花邊。在1935年,希特勒告訴德國衛生領導者,他打算利用戰爭作為掩護,清除德國的精神病患者。他曾考慮將精神疾病的安樂死納入早期法案中,但他放棄了這個想法,因為這可能會造成「太大的轟動」。當希特勒下令的時候,精神病患者在波蘭被殺,主要是通過槍擊,但也有一些是用毒氣。
希特勒的那份備忘錄至今仍然存在,裡面是幾句字跡模糊的私人信紙上的字—只有他的名字和納粹的標誌。安樂死行動在德國境內會奪去大約20萬人的生命,而在佔領區則有30萬人。這個數字中包括五千到一萬名兒童。安樂死會殺死大多數非猶太人,但也會啟動並使針對猶太人的死亡行為成為常規。至少有一名兒童在盟軍佔領期間被安樂死。
一位歷史學家的話,在最終解決方案之前,「希姆萊將大規模的殺戮外包給了安樂死部門。」
我在此強調的觀點,最早是由歷史學家卡梅隆·門羅(Cameron Munro)提出,他是柏林 Tiergarten 4 協會的負責人:沒有任何術語能完全捕捉納粹安樂死的演變範疇。它始於兒童,然後成為更大的成人 Aktion T4。T4 主要指的是在1939年德國和奧地利的六個精神病院內發生的毒氣室殺戮。隨著 T4 的推進,野生安樂死展開,而在這一切中,子行動 14f13,將 T4 的「評估」醫生送至集中營。納粹在佔領國的行動中,進行的精神病殺戮由被稱為 Einsatzgruppen 的納粹流動軍事部隊進行。1944年,啟動了 Aktion Brandt,這其中包括了在轟炸後殺死壓力病患者的德國婦女等。
兒童行動的啟動是從一名叫「嬰兒K」的嬰兒開始的。嬰兒K出生時失明,缺少一條腿和一隻手。他的父母稱他為「怪物」。1939年,K的父母請求希特勒讓他們殺掉這個孩子。希特勒派遣自己的醫生卡爾·布蘭特去檢查這個男孩。在布蘭特的批准下,嬰兒K在五個月大的時候因致命過量而死。
嬰兒K的死啟動了一項針對身體殘障兒童的殺戮計畫。到1939年8月,醫生和助產士被要求報告「畸形」嬰兒,報告者經常獲得補償。大多數孩子會像嬰兒K一樣,在醫院死亡。手段包括藥物和飢餓。參與計畫的醫院設立了殺戮單位,稱為「特殊病房」或「兒童病房」的委婉說法。『特殊』這個詞令人感到納粹的殺戮計畫, 在這些計畫中,Sonderbehandlung或「特殊處理」意味著死亡,Sonderkost或「特殊飲食」則意味著饑餓。通常情況下,醫生會給予類似巴比妥類藥物的藥物慢慢注射,導致死因被記錄為肺炎,這在肺部放慢後出現。
納粹政府對於這些計畫保持絕對保密。但是它用宣傳不斷轟炸人民,關於「劣等者」及安樂死的價值。影片、海報和新聞報導都集中在住院的高成本,甚至殘障人士希望死亡的渴望。機構提供了參觀。某部宣傳片名為《Dasein Ohne Leben》,即「沒有生命的存在」,在索嫩施泰因拍攝,卻從未公佈,因為在此計畫轉移至集中營之前。這部影片由保羅·尼切(Paul Nitsche)等人配音,結尾總結道:「一個不幸的存在的面容,因為無法治愈的精神病和非人道的生存而扭曲和折磨,最終在溫和的死亡中平靜下來,這最終帶來了幫助、救贖。」
學校的教科書給孩子們提出這樣的問題:「建設一個精神病院需要600萬馬克。可以建幾個每個15000馬克的安置所?」或者「一個精神病人每天的費用是4馬克,一個殘疾人5.5馬克,一個罪犯3.5馬克。對於一名公務員來說,每天只有大約4馬克的工資……想像這些數字。」
一名SS軍官在埃格夫林格(Eglfing)巡視時說,該機構應該在入口處安裝一台機槍,這句話使董事赫爾曼·范南米勒(Hermann Pfannmüller)感到高興。范南米勒是一名精神病學家和神經科學家,這位冷漠的男子戴著厚厚的圓眼鏡。如果我給你他的照片並稱他為20世紀早期的德國精神病學家,你可能會猜測他是佛洛伊德的信徒。實際上,他是一名狂熱的納粹主義者,並堅信兒童安樂死。一名名叫路德維希·萊納(Ludwig Lehner)的教師巡視了埃格夫林格,並在稍後的證詞中表示,范南米勒自誇使用「自然」的饑餓手段來殺死他的病人,他舉起一個「瘦骨嶙峋的孩子」就像舉起一隻兔子,預測這個孩子會在兩到三天內死去。萊納對這位「這個胖胖的、帶著微笑的男人,手裡抱著抽泣的骷髏」感到厭惡。稍後,在審判中聽到這段證詞時,范南米勒表示他「從未在那種時候微笑」,並且他「從未有過肉乎乎的手」。
范南米勒導致數百名兒童的死亡,並將超過兩千名患者轉移至安樂死中心。他在1951年受審,判刑四年。最終,法庭同意了這位醫生的邏輯,宣稱他因為使用飢餓,因此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謀殺者」。
安樂死迅速擴展至 Aktion T4 和成人。它的領導者設定了在德國境內結束70,000名殘障人士的生命的目標,這大概是被安置的人的數量的粗略估計。這一目標需要超越直接的醫院病房來完成。Aktion T4在柏林的一個優雅社區中,一棟竊取自猶太家庭的城市別墅的四號Tiergartenstrasse設立了辦公室。四號Tiergartenstrasse如今已不存在。在照片中,它看起來有點像我的維多利亞風格的房子,挺拔的,帶有拱窗和大量的裝飾。
但將德國的安樂死與大屠殺分開是錯誤的。後者不是一個開關,而是一種可怕的演變。T4是第一個針對特定「不受歡迎」群體的納粹計畫。即使在不小心的T4選擇過程中,猶太人也有特殊地位——不是因為他們能夠工作,經常根本不會被檢查。到1940年夏天,所有猶太精神病患者都被殺死。他們的死亡甚至不值得獲得其中一封T4的虛假慰問信。
大屠殺的劇本和理由來自這一波波機械化的殺戮。這些人員和技術也如此。大多數T4的醫生都轉向了大屠殺。
在1941年秋季,T4作為一個官方計畫停止,注意力轉向了大屠殺。決定「解決猶太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的萬維會議在1942年1月召開。隨後,啟動了一個名為Aktion Reinhardt的計畫,建立了僅供殺戮的死亡營。這些營地中的前三個——比爾澤克(Belzec)、索比堡(Sobibor)和特倫布林卡(Treblinka)——在波蘭建立。這些營地將奪去150萬人的生命。最多的死亡人數發生在特倫布林卡。
T4為死亡營提供人員——醫生、建築工人、操作員和管理者。所有這些工作人員都必須讓死亡營變得可接受,或不僅可接受的工作場所。當然,更大的行動吸引了更多的工人;許多營地的業務由納粹的Schutzstaffel(SS)進行。但T4提供了醫療和毒氣室的專業知識,以及許多營地的領導。許多T4的醫生也轉移到像奧斯維辛這樣的集中營,該集中營最初是一個集中營,後來演變成死亡營。
我們自然假設納粹醫學在戰前是殘酷且粗糙的,因為它最終導致了如此可怕的後果。但事實並非如此。在1920和1930年代,德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諾貝爾獎得主,在許多科學和醫學領域領先世界:癌症研究、技術、飛機發展等。德國醫學首先認識到並試圖預防如石棉這樣的物質的危害。它進入了許多當前的領域,如食用全穀物和使用植物藥。達豪不僅擁有一個集中營,還有一片藥用植物的土地。德國有異常多的女性醫生,其中一位在紐倫堡受審。
在某些方面,德國的成功為德國的邪惡鋪平了道路。公眾對癌症和石棉中毒等問題的關注使得微小且不可檢測的毒素進入身體的語言變得可怕。猶太人和吉普賽人及辛提人變成了病毒、細菌,成為肉體中的毒素。借用歷史學家羅伯特·傑伊·利夫頓的話,安樂死和大屠殺的核心觀念是,殺戮可以代表的不僅是破壞,而是治癒的至高表現——通過殺死個體,醫生清洗了國家。這些極端行為是新的和不可言喻的,但這些觀念並不是。
德國的醫學倫理法律也很嚴謹,醫學院有倫理課程,醫學教科書中有倫理討論。它們的倫理標準是西方最嚴格的之一。1900年的法律禁止在沒有同意的情況下進行醫學實驗,包括未成年人或任何無法給予同意的人。1931年頒布的法律,在《遺傳病預防法》之前兩年,加強了對兒童進行實驗的制裁。在某些方面,這些法律的某些方面超出了紐倫堡法典的標準。在我對納粹醫學的廣泛閱讀中,沒有發現任何人曾在安樂死期間提出過這些規則應該被暫停。它們只是被野心、貪婪和為國家服務的觀念所碾壓。
T4的影響還在心理上。德國歷史學家戈茨·阿利(Götz Aly)寫道:「我堅信,即使對1940年安樂死謀殺的有限抗議也會妨礙1941年系統性種族滅絕的發展……如果人們在親屬被謀殺時都不反對,那麼他們很難期望對猶太人、吉普賽人、俄羅斯人和波蘭人的謀殺表示反對。」
特倫布林卡審判的首席檢察官阿爾弗雷德·斯皮斯,花了數月時間與德國第二大致命營的管理者一起工作。他深信安樂死計畫不僅是為了消除「病人」,還是讓醫生和其他人員習慣於大規模殺戮。庫爾特·弗朗茲(Kurt Franz)從在索嫩施泰因做廚師上升至特倫布林卡的副主任,這樣寫道:T4顯示普通人可以被說服去做可怕的事情,「不帶任何顧忌。」
大多數安樂死的醫生通過黨的渠道上升,加入了NSDAP(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納粹黨的正式名稱),而且通常還加入了SS。在德國,醫學是最被納粹化的職業;在1920年代,德國醫生中有一半加入了NSDAP。醫生加入SS的機率是其他專業的七倍。疾病成為了德國的語言;希特勒則成為「國家的醫生」。納粹宣傳也為精神病學創造了使命,將猶太人與精神疾病聯繫起來,根據德國精神病學家埃米爾·克拉佩林(Emil Kraepelin)的理論,認為猶太人精神不穩定,容易患精神病。
在NSDAP掌權之前,柏林擁有德國最高比例的猶太醫生——大約一半的醫生在那裡執業。但猶太醫生遍布德國各地。德國納粹化的醫學協會和納粹的種族法則將他們驅逐出醫療行業,這是一個大型的過程,但並不是一夜之間的事情。希特勒與情婦伊娃·布勞恩(Eva Braun)的關係始於1931年,到了1936年,他便把伊娃安置在他的山莊,伯格霍夫(Berghof)裡。布勞恩的姐姐伊爾莎(Ilse)在1938年之前曾為一位名叫馬克斯(Marx)的猶太醫生工作。伊爾莎和她的老闆是朋友,直到馬克斯不得不逃亡。這位醫生的真空使亞利安醫生的上升和更高的薪水變得可能。許多NSDAP的醫生在城市的經營中,積極或共謀地將前同事和前老師趕出工作崗位。
卡爾·布蘭特開始了T4,後來負責營地的醫學實驗。當時的他不過二十多歲,因為治療希特勒的副官威廉·布魯克納(Wilhelm Bruckner)而引起希特勒的注意。還有一些來源說,葛莉·拉烏巴爾(Geli Raubal)在事故現場。拉烏巴爾是希特勒的異母姐的女兒,年紀比希特勒小十九歲。希特勒對她的喜愛是他從未對其他任何女性展現過的強度,包括長期情人布勞恩。1929年,希特勒把二十一歲的拉烏巴爾搬進他的慕尼黑公寓,很可能這段關係已經發展到性關係。拉烏巴爾在23歲時死於自殺,原因可能是她想離開希特勒的強迫關注,或是因為他知道她想離開而殺了她。與此同時,布蘭特讓希特勒印象深刻,以至於希特勒邀請他成為他的隨行醫生,隨行陪伴他出行。
布蘭特英俊、優雅,並受到納粹聚會的喜愛。儘管他忠於黨派和元首,但在心理上依然是一名醫生,無論是選擇治療還是死亡。布蘭特十分欣賞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阿爾伯特·施韋策(Albert Schweitzer),曾打算隨施韋策成為醫學傳教士。起初,布蘭特反對使用毒氣,因為他認為安樂死的「處理」應該是醫療的,如同注射。
菲利普·鮑勒,另一位接受希特勒「元首命令」的受益者,並不是醫生,而是一位高級官員。鮑勒圓圓的眼鏡讓他看起來書卷氣十足,像一個傾向於研究哲學的人。他曾為拿破崙寫過一本讚美傳記,這或許是希特勒邀請他為他編寫自己的贊美詩《阿道夫·希特勒:簡短的生平》。這本小冊子旨在國際消費,充滿了「廣闊胸懷、心地善良和公正」等語句。
布蘭特和鮑勒引入了維克多·布拉克(Viktor Brack),另一位官僚(德國有一個有用的術語Schreibtischtäter,可以大致翻譯為「辦公桌殺手」),他和鮑勒在總理府工作。布拉克在進入黨之前經歷了多種工作,從農業到賽車,然後是他上升的根源——他作為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的司機,為德國的種族滅絕行動提供服務。像許多其他人一樣,布拉克將從T4計畫「畢業」,以幫助建立死亡營,攜帶他對毒氣室的專業知識,並實驗進行絕育,向希姆萊建議創建三百萬名絕育猶太人的奴隸勞動力。
這些人將精神科醫生維爾納·海德(Werner Heyde)和保羅·尼切(Paul Nitsche)分配為醫療領導人,後者是索嫩施泰因的主任。海德被指控導致十萬人的死亡,受到一位名叫「非常不受歡迎」的猶太檢察官的指控。他是雙性戀或同性戀者。納粹針對像他這樣的人;在集中營中大約有一萬到一萬五千名同性戀者死亡。在照片中,海德的臉無表情:他是一個沒有秘密或許多秘密的人。除了這個,海德還與許多其他致力於德國的男子相似,曾被另一位醫生描述為「一個真正的納粹,沒有任何顧忌」。
海德的性取向曾兩次被SS調查,但由於文件處理不當以及海德的強大朋友,第一次調查並未有結果。一位朋友是SS軍官,曾是海德的病人,名叫西奧多·艾克(Theodor Eicke)。希姆萊自納粹黨成立以來就認識艾克,艾克的座右銘是「寬容是軟弱的標誌」,自認為是「德國的惡魔」。希姆萊希望艾克接管達豪集中營,當時被關押的大多數是政治犯。阻礙艾克的是他的精神病入院。艾克與高級納粹官員進行了一場權力鬥爭,該官員宣稱他是「瘋子」,並將他關進了監獄。認識他的人形容艾克是暴力且不穩定的,這些特質讓他在一種情境下被視為瘋子,而在另一種情境下則是國家的合適人選。只有海德接受了艾克的理智。艾克感激地告訴希姆萊,他「本可以擁抱」海德。
希姆萊對海德的讚許頗為滿意,於是給了醫生一筆小費。前艾克的達豪集中營釋放了許多囚犯。這原本是一個殘酷的地方,但並不是後來的集中營那樣的地獄。艾克所謂的「達豪精神」給予了輕微的處罰與死亡,讓人印象深刻。這一切使得希姆萊對這一切都充滿了贊嘆,並將艾克放在納粹的集中營體系中負責。這些營地的日常殘酷程度,與艾克以及間接與海德的責任大有關係。
T4的啟動依賴於文書工作:如此多的文書工作。位於四號Tiergartenstrasse的中央審查過程比兒童行動的過程更為複雜。在1939年,問卷從柏林發送到全德國和奧地利的機構,然後回流到這裡,並被複製和分發。T4擁有一個官僚的信件、備忘錄和人員文書,還有它的問卷、運輸清單、藥物和毒氣罐的請求、受害者照片和醫療記錄。
T4的現場擁有秘書和一間間的檔案室。在戰後發現的一份文件中,包括像計算安樂死70,000人的成本這樣的資料,與十年內養活他們的成本相比。也許這是另一個兒童教科書的數學問題。
對於問卷,稱為Meldebogen,醫療人員必須報告任何住院五年或更長的患者,主要是被診斷為無望的精神病、梅毒精神病、癲癇、「弱智」或癡呆。醫生可以並且確實報告超出這些建議類別的患者。他們報告患者的國籍,還有「德國血統」的標記。最關鍵的類別是工作能力。「無用的食客」通常被消滅。
T4總部雇用了大約三十名審核員。三名醫生對每個表格做出回應,這是一種象徵性的雙重語言:藍色的減號代表生命,紅色的加號代表死亡。這些標記被潦草地寫在表單側邊的黑色框中,並附上首字母。每位審核員的速度都很重要;他們的工資是以每張表格的計件方式支付,而不是按薪水支付。某位審核員在一個月內審核了1500個表格。頭醫生如尼切也掃描這些表格。死亡需要三位審核員中兩位的同意,但審查過程總是傾向於死亡。其他地方的醫生進行評估,將Meldebogen納入他們的另一項工作中。在埃格夫林格,范南米勒有時會處理超過一百份表格。
最初,大多數醫療機構的工作人員並不知道報告的理由。某些應答者誇大了患者的症狀,認為該計畫的目的在於將更健康的人去除,以便為戰爭勞動提供人力。
T4設定了七萬名死亡的目標,但沒有明顯的手段來達成這一目標。卡爾·布蘭特試圖用注射來實現,但死亡的過程緩慢,可能需要多次注射。希姆萊對毒氣作為快速、廉價的殺戮手段產生了興趣,這對於士兵來說壓力更小,因為他們經常在殺戮過多人後心理崩潰。1939年,納粹部隊接到命令,清空東部的精神病院,處理「無用的食客」。最初,患者被槍殺,站在一個大型坑前——一些人仍然穿著約束衣倒下。關於這一行動的報告傳達到了希姆萊那裡,告訴他這樣的行動讓部隊感到不安。槍支也消耗了珍貴的彈藥。
於是,第一個用於大規模死亡的毒氣室於1940年1月在柏林附近建成並進行測試。該地點建有第一台焚燒大型屍體的焚化爐及專門的擔架,以便在不過多接觸的情況下轉移那些屍體。這些建設是由維克多·布拉克的辦公室負責。該地點是一所古老的布蘭登堡監獄。T4管理者克里斯蒂安·維爾特(Christian Wirth)是一名木桶工的兒子,管理著實際的建設。維爾特隨後會轉移到T4地點格拉費內克(Grafeneck),然後負責索比堡和特倫布林卡——這是一個在艾克的模式下的男人,綽號「野蠻基督徒」。
鮑勒提出了一個想法,將房間偽裝成淋浴間,可能是布蘭特和德國化學家阿爾伯特·維德曼(Albert Widmann)的貢獻。患者以團體方式裸體進入大型淋浴,這對於受害者來說似乎是合理的。密封的房間也是如此。工作人員在進入時會給受害者毛巾。通過一個不顯眼的開口,將一氧化碳通過管道引入,這來自於一輛汽車。來自附近一個精神病院的十八到二十名患者被帶入進行測試。觀察者透過小窗戶觀看。淋浴的噱頭成功了。受害者自願進入,安靜地死去,屍體被悄悄燒毀。
布蘭特的顧慮被克服。他稱測試的結果為「醫學上的重大進展」。布蘭特預測,世界各國將採納這項技術,正如厄恩斯特·魯丁(Ernst Rüdin)預測的那樣,在納粹主義成功後,世界將進行安樂死。
大多數人已經對大屠殺的故事習以為常,以至於在這一時刻很難不感到顫抖:當時在觀景窗前的那些人,等待著一個毒氣室是否會成功。許多細節都消失了;這些人中許多人在戰爭結束時或之後不久就死去了。某些人,例如布蘭特,即使尚未決定使用毒氣的形式,也已經決定了這一點。然而,如果患者有強烈的拒絕,或者如果鮑勒沒有提出淋浴的想法,或者如果有人說服他放棄這個計畫,或者如果足夠多的事情出錯,布蘭特的懷疑可能會佔上風。布蘭特稍後與他的元首討論了成功的毒氣測試。
隨著布蘭登堡,開啟了一個深刻的轉折點,一個漫長而漫長的未來,至今仍與我們同在。
另一個轉折點,另一個未來,於布蘭登堡開啟。為了使T4建立殺戮地點,德國人必須同意殺戮德國人。或者至少不太在意。雖然T4以不成比例的方式殺死猶太人,但受害者仍然主要是亞利安人。如此多的死亡不可能永遠掩飾。大多數德國人對於殺死自己國籍的公民和殺死非德國的非公民之間做出了明確的區別。我懷疑沒有人會感到確信,殘疾和神經多樣性的污名會戰勝對消滅亞利安公民的顧慮。
如果公眾容忍這種殺戮,對於殺死非亞利安非公民的顧慮恐怕不會很大。在戰爭後期,特倫布林卡死亡營的一名守衛,他必須習慣幾乎任何事情,表達了無法置信行動品牌在德國殺死了成年亞利安人。顯然,希特勒的「偉大感覺」的抵抗可以被克服。
(内文照片来自GOO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