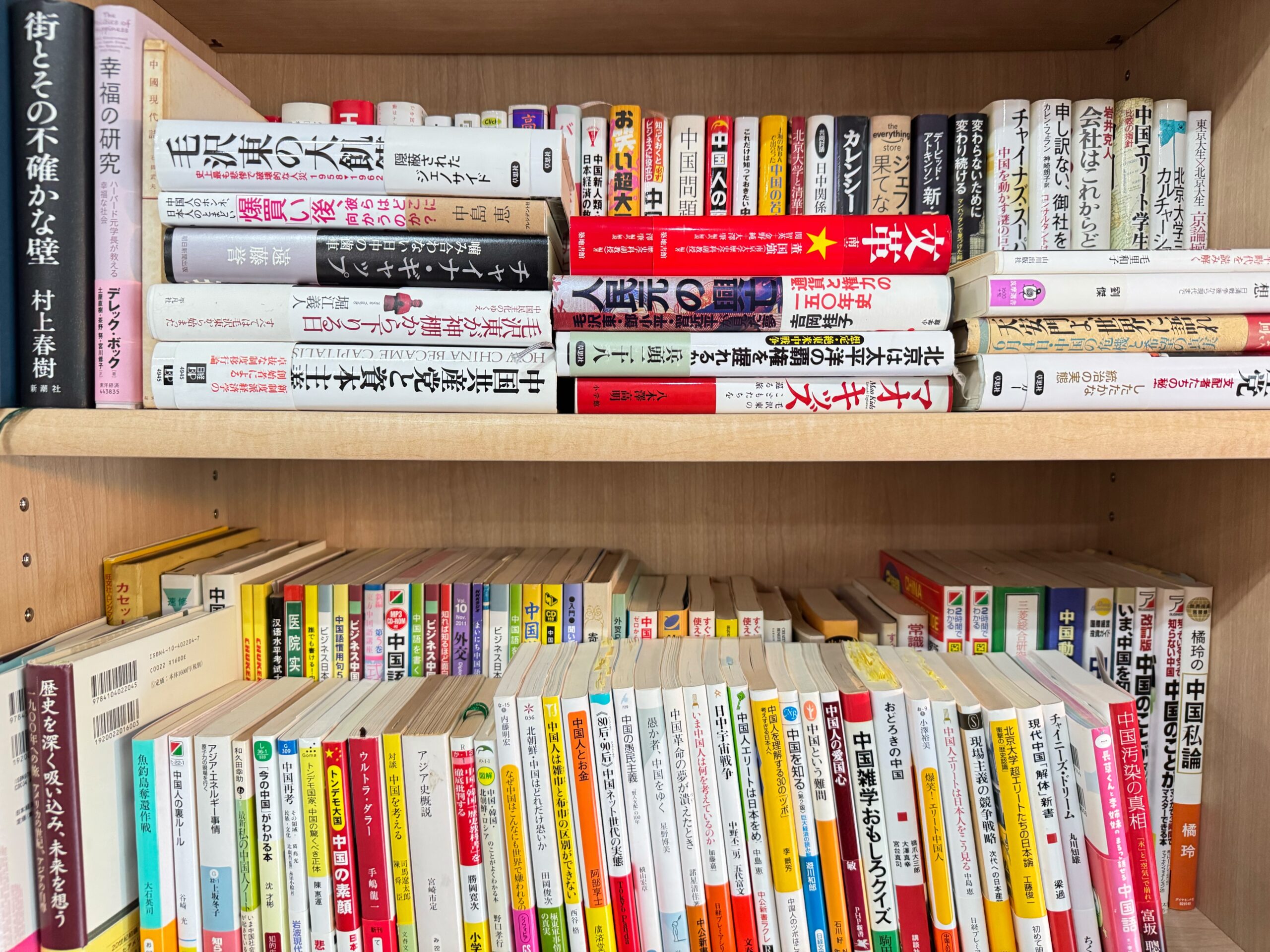東京六月,雨。延續著四月五月的陰鬱,淅淅瀝瀝,如泣如訴,不喜歡。
車站裡,萬人如海,我踽踽獨行,懷抱著每年六月的不適心情沉重。詩人說,四月是殘忍的,那六月是流血的,自1989年6月4日起流了36年,殘忍如雨,綿綿延延。
到書店,早和川瀨先生約好了的訪談。他是日經新聞社的編委,在上海、香港工作多年,中文流利無礙,屬知華一派。潤日的話頭說太多了,書店的經營也無非這樣,突然的,他問:「今年六四,你們有什麼紀念嗎?」。
五月廿四日,書店紀念了韓國的「六四」:光州事件。幾個年輕人和我看了電影《華麗的假期》,講述金大中與韓國民主的轉型模式,並為中國的「六四」禱告。光州事件看來義正辭嚴,但在朴槿惠李明博任內,也出現了醜化與污名。儘管有《五一八民主化運動特別法》在,正義並不理所當然。光州事件自發生後一直是政府禁忌,各種紀念、出版、討論均在禁止之列。高壓之下,死難者家屬和受傷倖存者奮起以收押者家族會、518光州義舉遺族會、518負傷者同志會等組織來追究真相,呼籲懲處元兇、賠償受害者。民間的各種示威、自殺抗議、甚至縱火不絕如縷,直到1987年的六月抗爭,終於破局。國會成立了調查委員會、特別立法之後、全鬥煥盧泰愚兩任總統定罪入獄。人家的「六四」有花戴,冤獄昭雪,復仇也成功了。成功的意義在於光州事件為民間的政治抗爭提供了一個持續不斷的道德基礎,彷彿不可撼動的憲法條款,逼得政府最終改邪歸正,才有了韓國的轉型正義。
一杯茶水過後,在香港工作過的川瀨先生不禁慨嘆,如今香港紀念六四已不可能了。是啊,從八九學潮爆發到六四開槍,無論明星助陣,還是市民捐款,香港是最熱心的。六、四過後,每年的紀念頑強不屈,已成舉世矚目的出口。現在呢,完全內陸一體,任何紀念都會被騷擾、噤聲。他們說這是一國兩制。
其實,為了紀念六四,早就請安田峰俊先生來書店錄了期對話。他是年輕一代寫中國的高手,多產,且穩健客觀,很受歡迎。他寫的《八九六四》還獲過獎。 安田說,日本對六四的態度起初是支持同情的,1990年的主流媒體報道得非常多,也很精彩。中國的民主運動也讓日本人刮目相看,爆發出對中國的強烈好感。影視劇與歌曲大量引入,許多人開始學習中文以了解中國。六四話題一直到1999年都保持著高水準的分析與紀念。之後三年多,歸於沉寂。等到2004年,重慶的足球亞洲盃賽出現反日暴動。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日本要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中國爆發了大規模反日遊行。隨著釣魚島事件升級,2008年奧運前的人權衝突,六四又成了話題,雖新意無多,卻已成政治晴雨,越來越「南京大屠殺化」了。以前多少中國人了解南京大屠殺呢,隨著政治交惡被釋放擴大,越來越政治化了。六四也一樣。它的現代性意義在1999年前還成立,對實際參與者來說,還有有理由,可很多人忘記了,更不要說隨著政治起伏言說六四了。
香港也是,和內陸經濟關係好時,加上開奧運的自豪感,每年紀念六四的人沒那麼多。到了2010年,大陸壓榨日仄,維多利亞公園紀念會達十萬多人!等到“雨傘革命”,情況愈烈,紀念六四愈多。當然現在維園被佔領,已不能紀念了。台灣本來也不關心六四,二二八事件更重要,畢竟那是其他國家的事。後來關註六四多了,也是兩岸關係起變化。這是安田先生清醒的洞見。但古往今來,學運只關乎政治嗎?那裡有沒有天生的公民抗命,有沒有對暴政的正當防衛,一種天賦人權的普世價值呢?
這都是他人的故事,中國人還是不能紀念六四, 或者都忘記了。以六、四精神為己任的人權律師、自由派學者、民間有誌之士成了打壓維穩的對象。六四風雲人物劉曉波堅持抗爭,在獄中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也有人抱怨六四打斷了歷史進程。對比光州事件,共產黨阻斷了六四記憶,實際抽掉了民間政治反抗的道德高地,讓所有的反抗碎裂成泥,無法形成一個以六四為基準的正義之網。這一點,他們「成功」了。成功地沒有認罪,規避了罪責。
六四30週年之際,香港編劇莊梅岩寫了舞台劇《5月35日》,好評如潮。前幾日,六四及劉曉波的研究者,中央大學的及川淳子教授熱心送我八月演出的海報,觸動的台詞是這句話:
「三十年來,生者與死者隔絕,活著的人忘記這件事,死去的人也消失在記憶深處。現在我孤身一人在這裡,不知道自己是否會被時間的洪流淹沒」。生者,死者,懼怕遺忘。
《華麗的假期》最後,屠殺的槍聲中,申愛反覆疾呼的也是:親愛的光州人民,請不要忘了我們…
不要忘記什麼?不要忘記“政府是暴徒,我兒子不是”,不要忘記“向老百姓開槍的軍隊,才是真正的叛軍”,就是記住罪,懲罰罪。
昆德拉說:人與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意味深長的是,韓國人勝利了,可金大中卻選擇了赦免,因為“要恨的不是人,是罪惡本身。”
是啊,只有看到六四正名才是勝利,看到罪人受懲才撫慰人心,假若死亡明天來臨,看不到呢。共產黨理應付出犯罪的代價,但也不能重要到俘獲和支配我們心靈的程度,我們對惡、對世界的態度不能取決於最壞的那一部分,而是應該像馬丁路德所說的那樣:即便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也要走出門去,懷著永恆的盼望,親手栽下一顆小樹苗。
東京局外人書店
2025年6月4日
(本篇為作者個人觀點分享,不代表本臺立場與意見,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建議或主張)